
文/梁志華
對香港電影美術的首次系統整理:
前文提到,新書《無中生有——香港電影美術及服裝造型展全紀錄》讓讀者反思,電影美術與文章寫作,同樣需要有具體的「畫面」呈現故事和背後的世界(觀);兩者背後的創作人亦需要有對事物的好奇心和探究精神。
香港電影發展曾有一段輝煌的時期,觀眾當然希望它能夠繼續如繁花綻放,這一次我們就借助《繁花盛放:香港電影美術 1979-2001》,追尋首次由「香港電影美術學會」系統整理的香港電影美術歷史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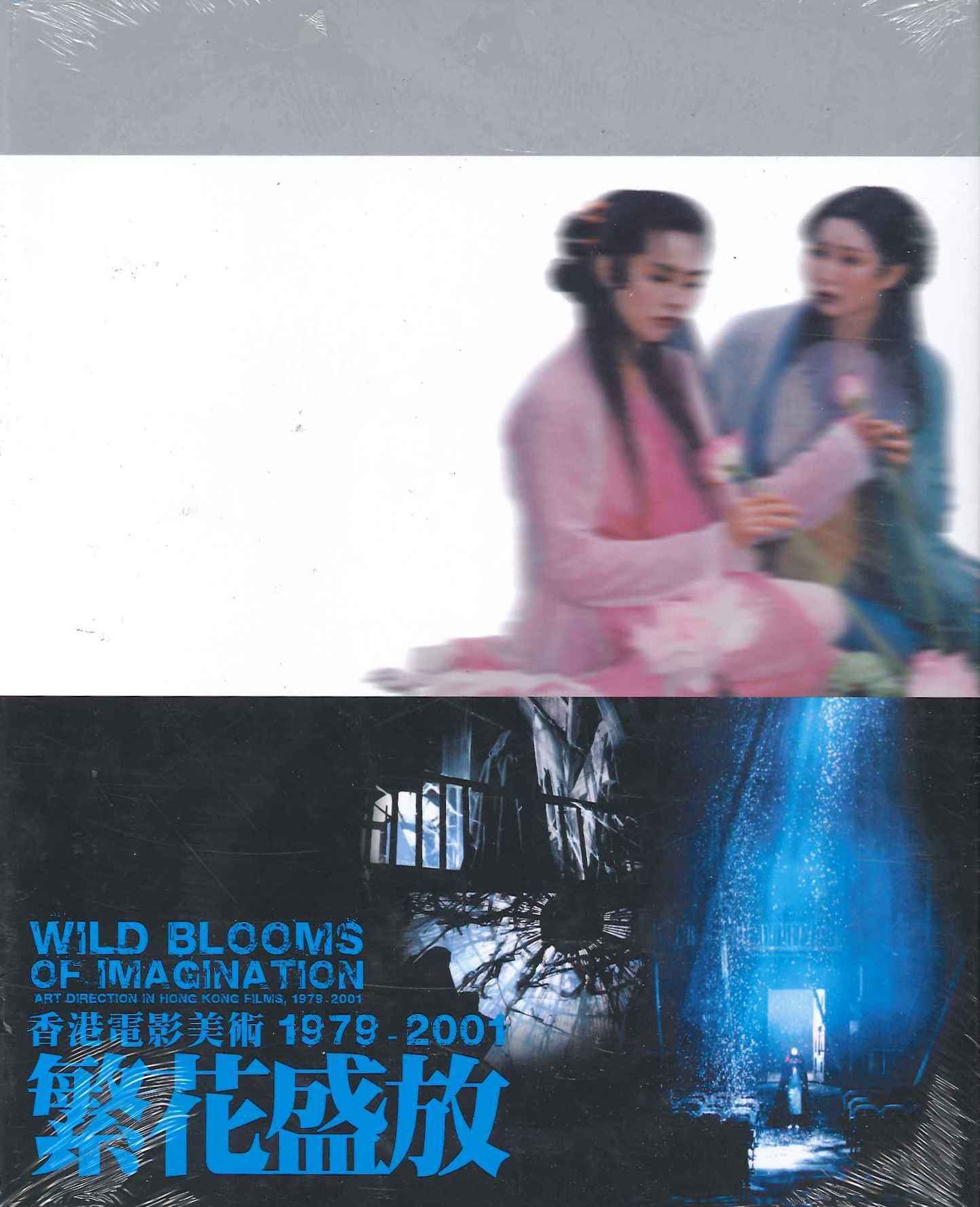
(圖片取自網絡)
築夢人眼中的香港電影美術:
通過訪問和整理香港電影美術指導(以下簡稱美指)和導演等,讀者了解築夢人對電影美術的觀點。以下試列數則供同工參考:
(一) 電影美術是流動的顏色:
〈阮玲玉〉的美指朴若木:

(圖片取自網絡)
給我五分鐘,我帶你進入我的世界。……電影美術就是流動的顏色,因此在剪接上,我們會用同一個方向,例如上一個鏡頭演員向右轉,下一個鏡頭是一輛車經過,都是同一個方向的,這便予人一種很流暢的感覺。
(二) 化抽象為具體:
前香港電影美術學會會長雷楚雄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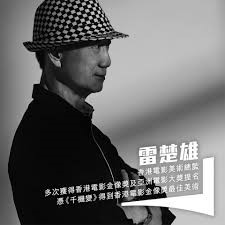
(圖片取自網絡)
我們的工作就是用視覺的、具體的手段,將抽象的概念表達出來,以營造一個氣氛。氣氛是很空泛的,它是很多東西加起來的結果。……所謂「電影美術」,是指在任何一格菲林裏所看到的實物和色彩……。
(三) 看不見的虛實美學:
〈唐朝豪放女〉的導演方令正:

(圖片取自網絡)
與中國人談虛實是很有趣的,正如道家講:道可道,非常道。他們用的是「遮撥」的方法,不斷否定:不是這個意思,但又不告訴你是甚麼含義,從而烘托出一個真實來。好像講「留白」,如果你不畫一隻蟋蟀,你怎樣講「白」呢?電影也是如此,很多人祇看到看見的東西,卻看不見背後看不見的,這其實才是導演要說的。
香港電影美術的精彩瞬間:
你有心愛的香港電影名單嗎?下面試列舉部分經典,從中亦可以思考對寫作教學有哪些啟發:
(一) 〈愛殺〉的顏色與象徵:
〈愛殺〉(1981年)給譽為確立香港電影美術指導位置與明確職能的作品。美指張叔平說:「導演要求一套很鮮明、很簡單、很基本的色彩,於是我和他逐場討論,定出這個色系,主要是試圖運用顏色去表達人物的個性和心理反應。……林青霞的衣著色調是慢慢地轉變,……紅藍二色同時出現可以代表人物精神分裂的狀態,紅色又象徵性及死亡等。」
(二) 〈花樣年華〉的鏡子與窺視:
〈花樣年華〉(2000年)的拍攝場景很小,為了製造更多拍攝角度,特意在多處場景加上鏡子,以豐富畫面的層次感,突出人物內心的複雜性。美指張叔平說:「我喜歡一些角度多一點的場景,最不喜歡就是一眼甚麼都給看完。所以我會找一些可以透過一堵牆、一道門看進去,或者是一些有曲位、有柱子的,反正就是可以創造多些空間的場景。」而導演更將層次感推向極致,運用前景(強調、突顯)製造給窺視的電影語言。
(三) 〈癲佬正傳〉的凌亂與焦點:
〈癲佬正傳〉(1986年)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外景,所以重新搭建,搭好了木屋又要擺放周圍的環境。恰好最後在另一個火災現場找到一些電燈柱可用。美指黃仁逵說:「火燒後的電線杆就像一棵很奇怪的椰樹,是焦黑的。我們把八條燒焦的的電線杆移到拍攝現場,有了這些垂直的線條,使凌亂的畫面馬上有了焦點。」
結語——用得多 vs. 用得好:
電影是需要不同部門合力建構的作品,每一種的手法、技巧並非單獨存在,而是為了表達劇本的主題、呈現導演最想表達的信息。文章的各種寫作手法、修辭技巧同樣是為了促進文章的整體效果。一如電影,文章內色彩的運用,可以象徵人物的內心情緒;而成功設定文章的焦點,更可以引導讀者發掘作品的主題所在。手法用得多,效果不及用得好,你同意嗎?
一連兩期跟各位分享了兩本關於香港美術的新舊圖書,你是否會好奇:那些年,在尚未設有美指崗位的香港電影是怎麼樣的呢,我們稍後就介紹《佈景魔術師——陳其銳、陳景森父子的佈景美學》,好嗎?
——尋「美」.jpg)











 已複製鏈結
已複製鏈結